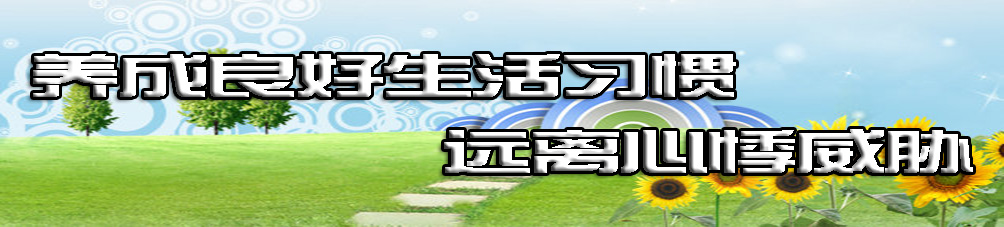不寐,又被称为失眠,是一种古老且复杂的病证名。它在古代的医学文献中有多处记载,如《难经·四十六难》称之为“不寐”,而《素问·调经论》则称其为“不得卧”。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,又被称作“不得眠”。这一病症的表现形式多样,有的患者难以入眠,有的则是寐而易醒,醒后再难入睡,有的则是时寐时醒,更有甚者整夜不眠或数夜难眠。这些表现虽各有特点,但总的来说,都被归为不寐或失眠的范畴。关于不寐的原因,有人错误地认为是由“心不藏神”所致。这种看法其实是不恰当的,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。为何这么说呢?因为心不藏神并不是不寐的直接原因,而是多种病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脏,导致心脏藏神功能失调的结果。实际上,不寐的成因多种多样,可能涉及生理、心理、环境等多个方面。例如,身体疾病如疼痛、呼吸困难等,心理因素如焦虑、抑郁等,以及环境因素如噪音、光照等都可能成为导致不寐的原因。因此,在治疗不寐时,必须全面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,找出真正的原因,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。只有这样,才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,帮助他们摆脱不寐的困扰。“心不藏神”的缘由深远且复杂,涵盖了我们生活中的诸多方面。首先,饮食与健康息息相关,若饮食不调,过度思虑或劳累,都会对心脾造成损害。心受伤则阴血暗耗,脾失健运,生血不足,心血更亏。这两者如同恶性循环,导致血虚神无所依,从而引发失眠等问题。再者,饮食习惯的失控,如肠胃受伤、宿食积滞,或饮食过度导致的痰湿内生,都可能扰乱神明,使得人难以入眠。正如《内经》所言: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。另外,个体的先天禀赋与疾病后的恢复状态,也是影响心神的重要因素。若先天不足,或病后真阴亏损,肾水不足,心火偏亢,心肾不交,都会导致神明受扰,产生失眠等症状。此外,个体的心理素质也不容忽视。心胆虚弱,善惊易恐,都可能使人心神不安,产生失眠。这种恶性循环,使得心神无法安定,失眠问题愈发严重。由于对不寐之因缺乏深入认识,我们在辨证和用药方面都存在误区。仅仅看到表面现象,而非本质原因,使得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。因此,吸取教训,深化认识,是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。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之后,我们认识到不寐分为虚实两类,即有邪多实,无邪为虚。这种分类方式,为我们提供了更准确的辨证和用药依据,有助于提高治疗不寐的效果。温胆汤在治疗不寐之症时,其效果之所以会出现悬殊,实则有深层次的缘由。以我所见,这其中主要涉及到两大方面。首先,实证不寐并非仅限于“胸脘胀闷,呕恶,苔黄腻,脉滑数或弦数”等痰火壅遏中焦之证,它还广泛涉及到“脘腹胀痛,嗳气食臭,纳呆乏味,脉沉实”的食积证,以及“苔白腻滑,脉不数”的痰湿中阻证。这些病症的成因并不完全相同,若一概以温胆汤治疗,自然只有痰火证能得到有效缓解,其余则难以奏效。其次,实证不寐常常是由食、痰、火三者相互交织、互为因果所致。因此,在治疗时,必须仔细权衡这三者之间的轻重关系,方能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。否则,治疗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,甚至无效。基于上述认识,我在临床上经常将二陈汤和平胃散相结合,作为基础方,并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进行加减。例如,对于痰湿较重的患者,我会加入藿香、白术、石菖蒲、川贝等药材以化痰祛湿;对于食积开始酿痰而偏于食的患者,则会加入神曲、麦芽、楂肉等消食导滞的药物;当食积酿痰和痰湿均化火时,则会加入竹茹、枳实等清热化痰之品,火邪甚者,还会加入黄芩、栀子等清热泻火的药材。这样的治疗方法,经过多年的实践验证,效果颇为满意,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参考。心脾亏损、心肾不交、心胆气虚,三者皆有心神不宁之证,临床表现为不寐、心悸、多梦等。然而,它们之间的病因与病机却各有侧重,不可混为一谈。心脾亏损,其核心在于血虚。心血不足,难以为面舌所荣,故见面色萎黄、舌质淡白。心血不足,心神失养,则心悸多梦。此外,脾虚健运无权,食少便溏,倦怠乏力;脾虚统血失职,则肌衄、妇女行经量多、崩漏等证亦随之而起。治疗当以补血养心、健脾益气为主,归脾汤正是此证的首选方剂。心肾不交,其根本在于阴虚。肾阴不足,水不济火,心火独亢,故见口干咽燥、心中烦热、舌红苔少等阴虚内热之症。肾主骨生髓,藏精,肾阴不足则骨失所荣,髓海不足,故见腰酸腿软、头昏耳鸣、遗精等症。治疗当以滋阴降火、交通心肾为主,朱砂安神丸、交泰丸等方剂可随证选用。心胆气虚,其关键在于气虚。气虚则心神失养,胆气怯弱,故见自汗、少气、心中空虚、惕惕而动、善惊易恐等症。治疗当以益气镇惊、安神定志为主,酸枣仁汤和安神定志丸均合病情。综上所述,心脾亏损、心肾不交、心胆气虚三证虽有相似之症,但病因病机各异,
临床表现亦各有特点。医者需细心辨析,抓住其特点进行辨证施治,方能药到病除。
辨证之难,又在虚证和虚实相兼
“治不寐难,难在何处?”前面已经谈到,难就难在治疗前之辨证,因为,辨证是治疗的前提。没有正确的辨证,就没有合理的治疗。然而,就不寐来说,我认为,辨证之难,又在虚证和虚实相兼方面。
其理由是: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。若辨不清虚在何脏,是阴虚、阳虚、还是气虚、血虚,而妄用补药,则不仅补无目的,治无效果,浪费药物,而且易把阳虚当气虚、阴虚当血虚治疗,结果,就会加剧病情,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;
虚证不寐,犹如迷雾中的行者,难以寻觅其真实的路径。这病症往往如同狡猾的狐狸,巧妙地藏匿于多脏之间,让人捉摸不定,难以捉摸其踪迹。即使我们已经洞察其虚弱的本质,却无法准确判断其虚弱所在的主要脏腑和次要脏腑,这无疑加大了治疗的难度。我曾遇到一位姓文的不寐患者,其症状繁多,犹如一团乱麻。他感到倦怠乏力,食欲不振,微有呕吐,大便稀薄,同时还伴有五心烦热,腰痛绵绵。舌淡,脉细弱,这些症状都指向了虚弱的本质。然而,我在治疗时,由于没有清晰地辨别出脾虚和肾虚症状出现的先后顺序,错误地使用了八仙长寿汤,结果导致患者腹泻加剧,每日达到五六次。这个失误让我深感痛心,也让我明白了治疗虚证不寐的重要性。虽然后来我用六君子汤加山药、黄芪成功止住了腹泻,又用八仙长寿汤治愈了患者的不寐,但这个沉痛的教训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它提醒我,治疗虚证不寐时,必须细心辨别,精确判断,才能确保药物直达病所,取得理想的疗效。虚实兼杂的病情,常常如同一幅交织的画卷,难以一眼看清其全貌。在治疗时,医生必须如同细心的画家,仔细分辨每一笔、每一划,才能准确地把握虚实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虚实之轻重,标本之缓急,都需要在心头权衡,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。当实证为主,虚证为次时,如同大树的主干坚实,但枝叶稍显凋零。此时,治疗的首要任务是驱邪,如同修剪枯枝,让树木更加挺拔。待实证得到控制后,再逐渐补虚,如同为树木施肥,使其枝叶繁茂。而虚中挟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,它如同一片荒芜的土地,虽然表面看似贫瘠,但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矿藏。在治疗时,既要补虚,如同为土地施肥,使其恢复生机;又要兼顾实证,如同开采矿藏,让地下的资源得以利用。若只知补虚而不知驱邪,或只知驱邪而不知补虚,都如同盲目开采或盲目施肥,不仅无助于病情的恢复,反而可能加重患者的痛苦。让我以一则治验为例来说明。周某,一位65岁的女性患者,长期失眠多梦,腰痛绵绵,双目干涩。这是肝肾阴虚的典型表现。然而,在诊前3日,她突然出现呕吐症状,吐出物为饮食物及痰涎,甚至连喝水也会呕吐。苔白腻滑,脉细数。这是痰湿内蕴之象。在此情况下,痰湿证急,必须先驱邪。我选用陈皮、云苓、半夏等药物,以化痰止呕。2剂药后,呕吐症状得到控制,苔退大半。此时,痰湿虽未尽,但阴虚之证已昭然若揭。于是,我改用杞菊地黄汤合二陈汤加川贝母,以滋补肝肾之阴,同时继续化痰。4剂药后,患者痊愈。这就是虚实兼杂病情的复杂之处。医生需要准确判断虚实之间的关系,制定出恰当的治疗方案,才能使患者早日康复。在临床上,治疗不寐症时,我们需要特别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dswth.com/rhzl/23186.html